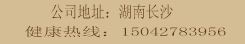![]() 当前位置: 海马 > 海马的形状 > 北京腔大院文化与华语影视
当前位置: 海马 > 海马的形状 > 北京腔大院文化与华语影视

![]() 当前位置: 海马 > 海马的形状 > 北京腔大院文化与华语影视
当前位置: 海马 > 海马的形状 > 北京腔大院文化与华语影视
理想国按:
好些年前,看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一直有一个疑惑:为什么在那样一个特殊年代,这群小孩活得这样无所事事、张扬肆意?
要再过几年,才知道这群小孩不是普通人,而是北京大院子弟。他们的所作所为,固然是因为特殊年代,但也离不开他们这一重特殊身份和背后的特殊文化——北京“大院文化”。
北京大院子弟,或者说北京大院文化,不知道读者朋友知道多少?固然它是特殊政治环境的产物,有着深深的特权文化的时代烙印,但它曾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北京文化,尤其是影视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从这里走出了一大批我们熟悉的人物:陈凯歌、田壮壮、姜文、冯小刚、管虎、葛优、梁天、英氏兄弟等。
不过如今,北京大院文化对于华语影视的影响终究还是随时代的变化日渐式微。
本文有点长,如果你对北京大院文化感兴趣,抑或你想知道华语影视发展的一段重要时期,那它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借鉴。
北京腔、大院文化与华语影视的渊源
(摘选)
文:开寅
1.
旧时北京有着南城和北城之分:南城是寻常百姓、普通体力劳动者和回民聚居的区域;北城则又分东西(老话中有东富西贵之说),往往是深宅院落相连,官宦大户、富商巨贾和知识分子寓居于此。
年的北平
南北两城不但形成了南俗北雅的两种不同文化,甚至连说话的腔调口音都不尽相同。
南城老百姓说话语速快如连珠炮,语调高昂吞音连音成了一种习惯,我们可以从老一辈的相声演员如侯宝林、郭启儒的相声中体会到它的特色;北城官宦富贵人家的子弟则语速舒缓,轻声慢语咬字清晰而又放松闲适,这一点当我们倾听孙道临早期的电影台词念白时,可以体会得到。
年新中国成立彻底改变了北京的格局。北京被定为首都后,中央政府陆续从全国各地调集了人数庞大、和当时北京人口旗鼓相当的各路人员进京。
这里面既有军人、党政干部和事业单位的职工,也有技术工人、知识分子、科研人员和教育工作者。他们并没有和本地人混居,而是大部分住进了由政府规划兴建的各种机关军队和国家部委事业单位的大院中。
北京大院的红色文化
这样的大院数量众多,绝大部分分散在城市的西部和北部,往往集办公、行政、教育甚至起居住宿为一体,形成了五脏俱全、无须与外界过多交流的“独立社会”。这就是后来大家所熟知的北京“大院文化”的诞生地。
在其中来自五湖四海的干部们都各操着自家的方言互相交流,而他们的子弟则在父母的方言和北京土话之中形成了带有革命色彩的新北京语言模式,甚至连说话的腔调和口音也有了变化,产生了吐字清脆悦耳、腔调抑扬顿挫、语速流畅利落的“大院口音”,构成了现在我们听到的北京话的基础体系。
而口音本身也成了阶层不同的身份区别标志:如果某个大院小孩心血来潮戏仿南城老百姓囫囵吞枣的说话方式,十有八九会挨父母一巴掌并被告之:“好好说话别跟嘴里含着个铁球似的”。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文革”开始前夕,由于北京北城的深宅院落大部分被清腾退转重新分配,官宦和知识分子文化已经接近消失。
而大院所孕育出的干部子弟和传统意义上的老北京人有了极大的差别。前者的特殊身份,让他们形成了不可逆转的精英优越意识,被革命激发出的理想主义情绪,又让他们和老北京含蓄谦逊质朴的文化习惯格格不入。
正是因为这样的差异,干部子弟和南北城的市民阶层出现了尖锐的对立、冲突、矛盾。年传奇的北京流氓“小混蛋”周长利之死便是这一冲突的标志。
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讲述了,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北京某军队大院的一群年轻人,共同经历的一段青春岁月。
北京的大院之所以可以孕育出与众不同的特殊文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干部子弟们衣食无忧和在社会阶层心理上高人一等的心态。同时由于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某些文化上的特权,他们比普通老百姓拥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接触到来自国外新奇而又具有反叛性的文化信息。
在“文革”期间,某位高层的子第听甲壳虫乐队的唱片、喜欢摇滚乐的传闻尽管从未被证实,但干部子弟可以通过特殊渠道听到西方和港台音乐的事实,是不能否认的。
崔健等一批中国最早的摇滚乐手,全部诞生在“文革”刚刚结束不久的北京,这和他们在七十年代得以通过大院这一特殊的生活环境和渠道接触到西方和港台音乐文化密不可分。
摄影师肖全镜头下的摇滚音乐家崔健
在电影方面,“文革”后期为了提高中国导演的技术和艺术素质,曾经反复组织导演们观看外国“内参片”。而到了七十年代末,每周在北京的各个军队、政府和机关的家属大院礼堂搞外国电影的“内部放映”几乎成了惯例。
正是通过这样的放映,干部子弟中不少人培养了对电影的最初兴趣,甚至产生了实践的渴望。
出身部队大院后来成为导演的叶京曾经讲过,他在七十年代末用一台借来的十六毫米摄影机拍摄独立电影的经过。这在当时普通市民阶层看来,已经是天方夜谭、几乎无法理解的行为。
而我们可以发现,在八十、九十年代活跃于影视圈的北京籍电影人,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干部子弟,这里不但包括出生于文艺干部家庭的陈凯歌、田壮壮、姜文、管虎、葛优、梁天、英氏兄弟等人,也有在大院中被文艺氛围熏陶而最终走上创作道路的“外来者”,其中就有王朔和叶京。
八十年代刘心武、陈建功、刘恒和王朔等北京籍作家声名鹊起,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北京文学流派,其中王朔在普通读者中影响力最大。
王朔
相比其他北京作家,王朔八十年代所有作品里的中心人物,都是六十年代以后的北京大院子弟:他们日渐失去了以往的特权和地位,以颓废和自嘲的无谓态度消解失落感,以接近于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意识猛烈嘲讽社会现实,以潜藏的理想主义情绪作为内心的唯一寄托。
在语言上,王朔第一个将北京大院文化语言落纸成书,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风:它既吸收了市民阶层犀利而富于想象力的表达思路,又兼容了文化阶层的精致趣味,同时一扫前者的庸俗粗鄙和后者的曲高和寡。
这种大院文化特点不但体现在王朔的文学作品中,也成了随后他参与创作的影视作品的标配。
年,改编自刘恒的小说《黑的雪》、由谢飞导演的《本命年》成了京腔文化进入影视作品的前奏。与刘恒的原作稍有一点错位的是,姜文扮演的主角表面是逡巡在北京胡同中无所事事的刑满释放人员,但内在气质却更贴近一个失落到谷底的大院子弟。
《本命年》中饰演犯人李慧泉的姜文
他外表冷峻但内心温柔,面对着一个飞速变化的陌生世界无所适从,不愿意放弃内心的原则,但又无法挽回那个已经逝去的、可以将理想主义付诸实践的时代。
姜文内心桀骜不驯的大院子弟个人气质,让这个角色不再是一个北京胡同串子那么简单,他成了整整一代因失去理想而孤身走向落寞的青年的象征。这样的人物和前述王朔作品中的特征不谋而合。
正是从《本命年》开始,影视作品中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北京大院文化特征:它渗透着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带着浓厚的批判现实价值观和个人理想主义气质;立足于某种卓尔不群的精英意识,却又时不时放低身段借用市民文化的表达手段;即便它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老北京文化中犀利调侃和诙谐幽默的表达方式,但它已经从纯粹的语言文字游戏中脱离出来,演变成指向性明显带着浅文本表达意识的“半精英半市民”文化。
2.
王朔是九十年代推动北京影视文化发展的“核心发动机”之一。不仅因为他的文学作品不断地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更因为他从九十年代开始,直接参与了很多影视作品的策划与创作。
年由他和苏雷、葛小刚、魏人、马未都等人撰写,赵宝刚导演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第一次完整抓住了新北京人在思维表达方式上的特点,剧中人物摆脱了以往影视作品中北京人单纯的油腔滑调耍贫嘴,变得字字珠玑语带双关,以前所未有的尖锐自嘲和嘲讽精神针砭时弊。这成了新北京文化正式亮相影视圈的标志之作。
年12月,我国第一部电视系列喜剧《编辑部的故事》北京首播。
由《编辑部的故事》出道、正式加入影视创作的,还有编剧冯小刚。他出生在干部大院,但少年时因为家庭变话题故又搬到了城里大杂院居住。
比起“根红苗正”、口吻极其辛辣的王朔,冯小刚的视角要温和许多,他更懂得贴近市民阶层的心理,展现人物富有温和情感的一面。
这一点在他给导演夏钢撰写的剧本《大撒把》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片中,葛优含蓄幽默、饱含温情的北京“暖男”形象让人耳目一新,它第一次让“温情”成为中国影视作品表达的核心情绪。
《大撒把》中饰演男主人公顾颜的葛优和饰演女主人公林周云的徐帆。
冯小刚得以迅速在影视界大展拳脚,还要依赖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对他的信任。后者的前身是成立于年的北京电视制片厂,在八十年代它就主导拍摄了《四世同堂》、《渴望》等带着浓郁北京色彩的电视剧。它发掘培养了赵宝刚、郑晓龙、李晓明等一批北京籍的电视剧创作者,成了北京电视剧导演和编剧的孵化器。
根据行内人打趣的说法,在电视剧制作超级火爆的年份,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会计和司机都被外聘成了编剧,足见它在影视圈内的影响力。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在电视剧产业还算刚起步的年,它做了一件让当时所有业内人士都大跌眼镜的惊人之举:将全部资产抵押获得的资金,投入拍摄了由郑晓龙和冯小刚联合执导、由姜文主演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而冯小刚正是通过这个宝贵的机会一跃成为导演。
《编辑部的故事》制作团队部分人员的合影,从左至右依次是葛优、冯小刚、王朔、赵宝刚。
在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体制之外,还出现了另一个电视剧制作团队,就是由英达领衔的英氏家族。他吸收了美国室内情景剧的形式而主导创作的《我爱我家》,成了最脍炙人口的京腔影视文化代表。
《我爱我家》的“文学师”梁左被王朔称作是“中国最具幽默素养的作家”,而英达不但自幼受到集演员、戏剧家和翻译家于一身的父亲英若诚的熏陶,还是“文革”后第一批留学美国学习影视的中国导演之一。
梁、英二人一中一洋组合所采取的入手角度,与王朔冯小刚等人皆有所区别:《我爱我家》重新利用了北京话作为方言所产生的魅力,深度挖掘了带着地域性色彩的市民文化趣味。它既有很强的地方特色,又在用辞和表达上通俗易懂,极易深入人心,这是它在全国产生轰动效应、在大江南北久播不衰的重要原因。
《我爱我家》还对中国的影视制作产生了启发式的连带效应:它使很多影视从业者意识到,在商业化制作逐渐成为产业的九十年代初,发掘带着地域性文化元素的作品,尤其是以方言主打的作品,是有可能在市场上取得良好反响的。
令观众难以忘怀的电视剧《我爱我家》
在《我爱我家》之后,英氏兄弟又接连制作了以陕西、上海和东北方言为主打的室内情景剧,把对地域性的强调作为制作的主要方向。
在年到年之间,“京味儿”商业电影电视作品如雨后春笋,电视剧《爱你没商量》、《海马歌舞厅》、《过把瘾》、《东边日出西边雨》,电影《无人喝彩》、《上一当》、《天生胆小》、《离婚大战》都成了火爆市场的作品,京腔影视文化达到了它的第一个高潮。
这些影视作品不但让北京籍的葛优、梁天、谢园等人成为热门演员(三人搭档联袂出演了大量影视剧),他们的京腔京韵也成为时髦的影视语言。一些非北京籍演员如上海人王志文、马晓晴,吉林人贾宏声,或者武汉人徐帆,为了表演的职业需要也开始将北京腔模仿得惟妙惟肖。
与此同时,身为大院子弟的姜文却从这个京味影视创作热潮中抽身而出,他埋头将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改编成了电影剧本《阳光灿烂的日子》。影片不但入围了年的威尼斯电影节,少年夏雨还夺得了最佳男主角奖。
《阳光灿烂的日子》剧照
对于《阳光灿烂的日子》的解读和分析已经长篇累牍,但鲜有人提到的是,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正面表现大院子弟形象的电影。
与王朔原著交织着欲望的阴郁和冷峻截然相反,姜文呈现在银幕上的是一出充满青春活力和火热理想主义情绪的视觉语言盛筵。
他在影片中对大院集体生活和躁动的暴力宣泄的梦幻般的憧憬迷恋,代表了相当多北京大院子弟的真实心境。同时他并未停留在对他们优越心态的表面刻画,他意识到逝去的理想主义与九十年代扭曲的价值观和人性堕落之间所形成的巨大反差,他有意识地以过去对照现在,在两个不同的北京之间找到了某种带着强烈宿命乡愁意味的激情快感。
正是这个明确的意图,让《阳光灿烂的日子》从王朔式的批判现实和冯小刚式的温情幽默中脱颖而出,形成了北京影视文化中的第三个标志性情绪:激情,并借助它将地域性的北京文化托上了艺术化的高峰。
九十年代的北京同样也是中国地下先锋文化的中心。第六代导演张元抓住了这些暗潮涌动的异样元素,将它们汇集成了反文化拼贴图景式的影片《北京杂种》。
我们在其中看到了八十年代就活跃在北京地下音乐圈的著名人物:崔健、窦唯、骅梓、张楚、臧天朔,而那带着大量无意义的语气助词和充满了咒怨愤怒的脏话成了影片的标志之一,这也是北京土语第一次以这样前卫先锋的方式登上银幕。
电影创作者和评论者同时发现,北京地域性文化的内核,同样可以为某种探索式的先锋影像和文本表达服务:充满反叛性的电影《头发乱了》、《长大成人》,九十年代少见的同性恋影片《东宫西宫》,王朔和冯小刚充满荒诞现实感的影片《我是你爸爸》,以及张艺谋风格转型的快意之作《有话好好说》,都让我们感受到了北京话和北京城市的整体氛围为影片带来的形式化魅力。
此时的北京影视文化已经在四个方向上同时展开:它既可以如《编辑部的故事》一样强烈地批判现实,又能演变为《我爱我家》、《大撒把》式带着浓浓温情的成功的商业化作品;既可以拥有《阳光灿烂的日子》式的个人激情的表达,又有能力容纳《北京杂种》这样低调冷峻的前卫意识。作为带着强烈地域性色彩的影视文化,它的可塑性和延展性是惊人的。
3.
在九十年代中期,当赵宝刚、郑晓龙和尤小刚等人以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为基地频出新作,博得阵阵好评的时候,冯小刚却跌进了他事业的低谷。他和王朔成立了“好梦”公司,趁热打铁推出了几部影视作品。
冯小刚,年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年金马奖最佳导演。
也许是受了王朔过分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态度的影响,他执导的电视剧《一地鸡毛》、《月亮背面》和电影《我是你爸爸》,都因为题材敏感或包含着强烈的负面情绪,遭到了禁播。
冯小刚也被扣上了“票房毒药”的帽子。他经过苦苦思考后,暂时放弃了批判现实主义式的带着尖锐嘲讽口吻的创作方向,重新开始借用“新北京话”所形成的语言魅力,并转向了银幕喜剧的创作。
冯小刚再次借用了王朔《顽主》小说的故事形式,以较低的成本拍摄了《甲方乙方》,并且第一次在宣传发行上套用了港台电影“贺岁片”的概念,影片大获成功。
随后,他又以相同的方式接连推出了《不见不散》、《没完没了》,每一部都在中国电影整体票房低迷的九十年代末大卖,他一扫此前的“霉运”,不但扬眉吐气,而且还成为拯救大陆电影票房成绩的灵药。
相比起冯小刚此前其他作品,在这三部影片中,他暂时压抑了撩拨暗郁现实的反叛冲动,把温情亲民的一面发挥到了极致。
冯小刚电影《甲方乙方》、《不见不散》和《没完没了》的相关海报。
他依然落脚在一些社会底层人民
转载请注明:http://www.haimaahm.com/gysc/6840.html